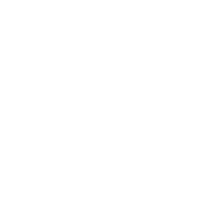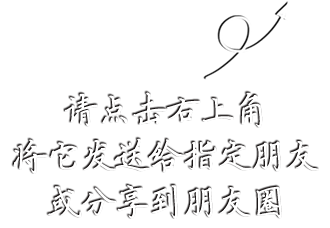|
|
|
粮瓮小史 |
|
|
|
| ( 2020-11-27 ) 稿件来源:新华每日电讯 说人解史 |
|
聂英杰
曾几何时,粮瓮的多少是庄稼人家底的象征,它见证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迁。对我们家来说,粮瓮无疑是一段酸甜苦辣的生活史。母亲曾讲,和父亲结婚三四年后,祖母才分家,当时我们家只有一口大瓮、一口小瓮和一个小瓦罐。粮瓮虽不多,困难年代瓮里却空空如也,一敲当当响。那些年,母亲总是发愁粮瓮何年何月才能盛满粮食。
后来,国家允许有自留地,以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,一下子唤起了母亲向往美好生活的劲头。母亲针线活计比较笨拙,庄稼活却是个“好把式”。她和父亲白天给生产队干活,闲余经营自留地,队里工分挣得多,自留地里庄稼也长势喜人,一口大瓮怎么也装不下。外祖父母得知后,送来两口光溜溜的大瓮,家中余粮才有了安顿之所。
当老人的谁不愿让孩子们过上殷实的日子。后来,家里出了事,小院的平静被打破,两口大瓮也被人抬走了。以至后来,每次队里分粮,母亲就指着仓库里的两口瓮反复念叨,那是咱家的,是你姥姥给的。说来也怪,从此我家再也没有为盛粮发愁过。家里姊妹多,只有父亲一人挣工分,口粮常常被扣,哪有粮食储存。记得一次家中快要断顿,母亲领着我和大妹妹,怀里抱着二妹子,乞求分点粮食来糊口……每当忆起那痛心的一幕,泪水犹如泉涌,生活的艰辛和磨难成了日后我努力学习与工作的动力。
时针很快转到了1976年,队里夏粮秋粮获得少有的丰收,我家分的粮食估计有1000多斤,人均虽不多,毕竟能吃上饱饭了。也是从那年开始,连续三年丰收,全家人把前所未有的兴奋化成一个急迫的念头,赶快买瓮制瓮。那年头村里掀起了抹制水泥瓮的热潮,这种瓮虽不结实可花钱少,我家便先后找人抹了五口大瓮,这在当时可是不小的家产。也是从那年起,我家隔三岔五能吃上白面条,过年还能蒸上两三锅馒头,我们姊妹七个别提有多高兴了,天天盼着过年。
1979年的冬天格外冷,人们的心头却热泉涌动。在村民半信半疑的议论中,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春风一路吹到了泜河岸边,吹进我们这个偏僻的小村,吹到庄稼人的炕头上。第二年包产到户变成现实,农民蕴藏的生产积极性一夜之间得以爆发。我家因为人多,分了12亩地,母亲带领一家老小披星戴月,辛勤耕作,打的粮食库仓里实在盛不下,干脆放到了屋里炕上、地上,家里简直成了粮食的世界,一家人都看傻眼了。
1984年,我家有史以来全年吃上暄腾腾、香喷喷的大馒头,一举告别了吃窝窝、红薯干的艰苦生活。母亲满含深情地说,旧社会连大户人家也没有今天的好日子。那几年,一股买瓮热又闹翻了小村,每至夏日傍晚,拉瓮的车子一到街上,就被乡亲们围得水泄不通。东家两个、西家三个,不大会儿工夫,三四车瓮卖得一干二净。几年间我家粮瓮达到了20多口,库房里一圈光溜溜的大瓮就像威武的罗汉那么壮观。生活的欢乐、日子的香甜,原先仓库里我家那两口大瓮,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。
1999年,村里又重新调整了责任田,家中人少了,地也少了,打的粮食自然也就少了,可日子却像开花的芝麻节节高。屋里那么多的闲瓮成了家中的累赘、碍事的东西,父亲和弟弟索性将多余的瓮丢到房前空地上,一任风吹雨打。不知是我生性多愁善感,还是瓮的命运牵着太多情感,每次回家看着、摸着伴我二三十年的粮瓮,心里总不是滋味。感情的潮水催促着我写下这段文字,来珍藏内心深处的记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