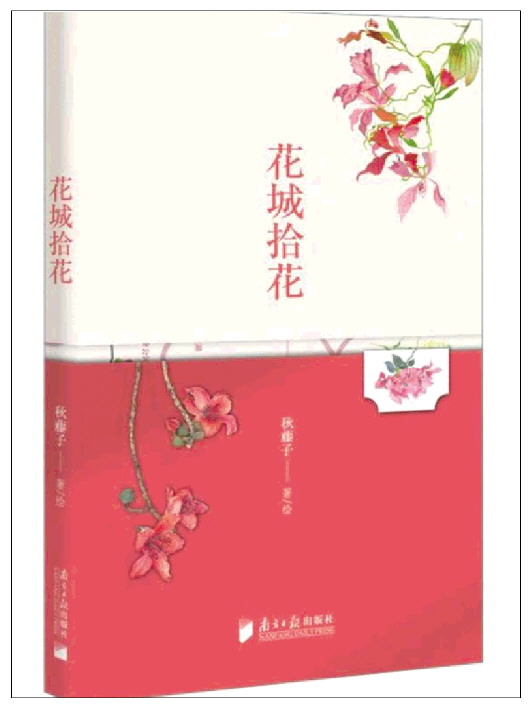|
|
|
 04版:权威发布
04版:权威发布
- * 李克强同志生平
 09版:草地周刊
09版:草地周刊
- * 任继周:“草人”不老
- *
新华组歌
 12版:神州风物
12版:神州风物
- * 身边的那片田野,手边的枣花香
- * 井陉寻古记
|
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“秋千” 读书笔记两篇 |
|
|
| ( 2023-11-03 ) 稿件来源:新华每日电讯 人文漫笔 |
 |
|
|
|
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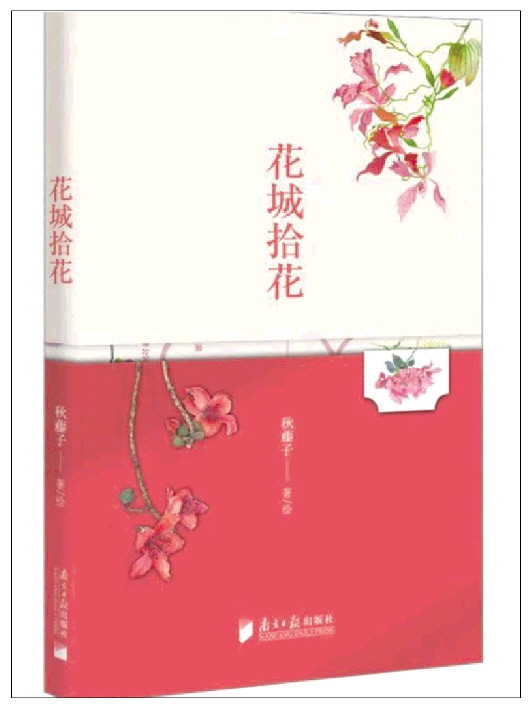 |
|
|
|
|
我们自己的“秋千”
日本作家荻原浩的小说《海边理发店》,我很喜欢。小说情节很简单,一对多年未见的父子相见却并未相认的故事。作为老理发师的父亲,离开家乡东京,来到僻静偏远的海边,开了一家小理发店,已经十五年。有一天,儿子突然来到理发店,是来告诉父亲他即将结婚的消息。几十年所有跌宕的人生经历和家庭恩怨,以及父子之间亲情的隔膜与交融,都浓缩在这个小小的理发店里涌动。
小说开头,先出现一架秋千,儿子一眼看到:“没有鲜花的院子里,立着一架被人遗忘的秋千,支架和锁链上都布满了红色的锈迹。”
这是作者有意的设置,方才如此先入为主。秋千,不仅起到小说情节的贯穿作用,更起到父子之间的感情,尤其是父亲对儿子复杂感情的描摹作用。
儿子小时候,在河滩公园荡秋千的时候,不小心摔了下来,河滩上都是石头,伤了儿子,在他的后脑勺上留下了一道缝过针的伤口。父亲担心儿子再到河滩上玩秋千会跌伤,便干脆买了一架秋千,装在自家的院子里。十五年前,父亲从东京把秋千搬到海边,安放在理发店的小院里。
小说结尾,父亲为儿子理发时,特意仔细看了儿子后脑勺上被针缝过的伤口,确认了这就是自己多年未见的儿子,禁不住突然问儿子:“您后脑勺上这缝过针的伤口,是小时候摔的吧?”
小说在这里,让儿子不禁望了望父亲,逆光中的父亲的脸变成一团黑影,他看不清父亲的表情。这一笔写得真好,看不清父亲脸上的表情,其实更动人,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。我们也就明白,为什么要在小说开头先设置一架秋千,而且,要让儿子一眼看见。一架秋千,串联起几十年的岁月,勾连起父子之间的感情,如此简洁,给漫长的时光和抽象的感情,都赋予了生动的形象。
读完《海边理发店》,我想起了孙犁先生的小说《秋千》。看小说的题目,就可以知道,这篇小说也写到了秋千。不过,写法不尽相同,秋千只是在小说结尾才出现,不像《海边理发店》那样首尾呼应。
《秋千》写一个十五岁的姑娘,日本鬼子烧毁了她家的房子,爹娘早死,从小吃苦,但是,她有个爷爷,曾经开过一家小店铺,有几十亩的地。农村定成分的时候,有人提起她爷爷的陈年旧事,要定她为富农地主。她一下子委顿了,和她一起的女伴们也一起失去了往日的快活,纷纷替她鸣不平。最后,她爷爷属于上一辈的事,她被定为普通农民。立刻,她和女伴恢复了往日的快活。那么,这快活劲儿怎么写?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她和她的这一群女伴的心情,还关系着她们的形象。
在这里,孙犁先生也运用了秋千这一形象化的细节,作为她们心情和形象的载体:
她们在村西头搭了一个很高的秋千架。每天黄昏,她们放下纺车就跑到这里来,争先跳上去,弓着腰往上一蹴,几下就能和大横梁取个平齐。在天空的红云彩下,两条红裤子翻上飞下,秋千吱呀作响,她们嬉笑着送走晚饭前这一段时光。
秋千在大道旁边,来往的车辆很多,拉白菜的,送公粮的。戴着毡帽穿着大羊皮袄的把式们怀里抱着大鞭,一出街口,眼睛就盯着秋千上面。其中有一辆,在拐角的地方,碰在碌碡上翻了,白菜滚到沟里去,引得女孩子们大笑起来。
有了秋千,一下子,就有了心情,有了场面,有了主客观两方面的镜头,姑娘们一扫以往的阴霾,那样明亮而生动起来。姑娘们的心情和形象,都在秋千上面闪现,要不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车把式观看,更不会有人翻车了。
同样是秋千,孙犁先生的秋千,和荻原浩的秋千,不完全相同。荻原浩的秋千,原来在海边并没有,是作者明显有意的设置,让秋千前后两次出场,让小说有了悬念和起伏;孙犁先生的秋千,原来就在村西头,只是最后出场,自然妥帖,恰到好处,点到为主,戛然而止。
可以看出,秋千作为小说中的细节,就是这样不可或缺,牵一发而动全身,起到情节所难以起到的作用。我们甚至可以忘记小说中具体的情节,却难忘这样动人的细节。
想想在我们的生活中,其实,也有类似秋千的细节,足以打动我们自己,令人难忘。我们在自己的回忆中,或在向他人的诉说中,便可以不再只是说感动、难忘这样抽象的词语,而多了这样动人形象又格外特别的细节。
是的,要相信,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“秋千”。
邱方和曾孝濂
邱方的新书《花城拾花》,和她的上一本书《花有信,等风来》一样,还是顽强于看花、拍花、画花和写花的执着之中。稍有区别的是,这本新书集中于广州的群芳谱,让其中一百六十余种广州人熟悉和不熟悉的花卉,争奇斗艳地绽放在一本图文并茂、印制精美的小书里。这本小书,让秦牧那本有名的《花城》的书名,有了还魂的魅力;让广州这座花城的别名,得到一次芬芳四射的彰显。可以说,这是一本比植物园导游图更丰盈别致的广州寻芳图,是一本继清人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后崭新的岭南新语。
读这本《花城拾花》,我想起曾孝濂先生。
曾先生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学家。之所以想起曾先生,是因为发现邱方和曾先生,真有很多相似之处。他们都是一样热爱并执着于看花、拍花、画花和写花;他们一样都是在退休之后,集中精力做这些事情的。只不过,邱方早,五十五岁退休后;而曾先生是在八十岁之后。在此之前,曾先生曾为《中国植物志》绘制植物标本,是其工作,而在八十岁时有了自己的时间,方才为自己的钟爱拾花试笔挥毫。
我不知道邱方退休之后的第一张画,画的是什么花。曾先生画的是鸡冠花。在这本新书中,邱方也写到了鸡冠花,她说:“鸡冠花可能是我们最为熟悉但又最没存在感的花了。公园里、路边有时会种上一片,貌不惊人甚至有点面目模糊,没人会为它呼朋唤友或停下脚步去细细观赏。”
曾先生最先画的,就是这种最不起眼的鸡冠花。鸡冠花,又叫雁来红,还叫老来红。知道了它的别名,我们也就明白了,曾先生为什么老来八十之后最先画了鸡冠花。尽管他早已经是有名的植物学家和画家,他为我国设计的花鸟邮票曾经风行一时。邱方在她的这本新书中说得对:“花的世界,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面镜子。”花与人,镜像互映。
邱方和曾先生还有相似之处,是他们对花的认知。邱方说:“花是人类历史最悠久的交流媒介,承载着对生命的和世界的认知,也附着了人们的万千情愫。”曾先生为他八十岁后所画的90种花和100种树出版画集,命名为《极命草木》。他说:“‘原本山川,极命草木’,是我们所的所训,极命草木,就是极尽所能地珍惜爱护一草一木、一鸟一虫,乃至所有的生命。”
邱方和曾先生更为相同之处,是他们对花的热爱,对画的热爱,是发自深心的,是致命的,是一生的。在谈到为什么如此钟情画花画树的时候,曾先生说:“我真的就是为画画这件事而来,为做这件事而去的。老了,病了,都不在话下。我只要一画画,就什么都不想,非常愉快,非常知足。”
我想,这也是邱方心里要说的话。她还不老,远不到曾先生一样的年龄,也没有病,如今腿脚爽快,还在四处乱跑,更是应该以曾先生为榜样,要“不在话下”地多画多写。因为,她和曾先生一样,都是为一生所钟爱的这件事而来的。《花城拾花》,不过是邱方所做的这件事中愉快的一笔。相信她会再接再厉。“对于爱花人来说,居花城是幸福的。”期待着她和曾先生一样,都抒写幸福的下一笔。

![****处理标记:[page]时, 字段 []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! ****](../../IMAGE/20231103/01/01-s.jpg)
![****处理标记:[page]时, 字段 []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! ****](../../IMAGE/20231103/02/02-s.jpg)
![****处理标记:[page]时, 字段 []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! ****](../../IMAGE/20231103/03/03-s.jpg)
![****处理标记:[page]时, 字段 []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! ****](../../IMAGE/20231103/04/04-s.jpg)
![****处理标记:[page]时, 字段 []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! ****](../../IMAGE/20231103/05/05-s.jpg)
![****处理标记:[page]时, 字段 []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! ****](../../IMAGE/20231103/06/06-s.jpg)
![****处理标记:[page]时, 字段 []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! ****](../../IMAGE/20231103/07/07-s.jpg)
![****处理标记:[page]时, 字段 []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! ****](../../IMAGE/20231103/08/08-s.jpg)
![****处理标记:[page]时, 字段 []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! ****](../../IMAGE/20231103/09/09-s.jpg)
![****处理标记:[page]时, 字段 []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! ****](../../IMAGE/20231103/10/10-s.jpg)
![****处理标记:[page]时, 字段 []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! ****](../../IMAGE/20231103/11/Page11-1500.jpg)
![****处理标记:[page]时, 字段 [] 在数据源中没有找到! ****](../../IMAGE/20231103/12/Page12-1500.jpg)